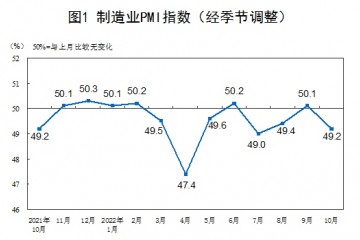“
在一个完整的悲剧人物身上,我们应该看到某种高贵的品性,那是一种仁慈或慷慨的品质,一种对自我身份的追寻,让他终究能够认清自我。然而黛玉缺乏的正是这种高贵的品性。从智力上看,她完全有能力获得这种自知能力,但她过分囿于自己的不安全感,因而未能从客观或反讽的角度来观察自己。于是,在小说里她尽管诗意地生活着,但其扮演的角色是为了表现无可变更的感伤可怜,为了充分展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在身体和感情两方面的毁灭。
”
本文摘自夏志清所著《中国古典小说》
第7章《红楼梦》,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夏志清(1921—2013)生于上海浦东,原籍江苏吴县。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抗战胜利后任教北京大学英文系。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1951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先后执教美国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等校。1961年任教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1969年为该校中文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文名誉教授。
“
林黛玉的悲剧性在于她那种
固执的不切实际与反常的自我矛盾
”
借用简·奥斯汀的话来说,这部小说中的女性,或以“理性”(sense)而出众,或因感性(sensibility)而闻名。在最接近宝玉的四个女性人物中,宝钗和袭人是事理明达之人,而黛玉和晴雯则是感性、神经质而不切实际的。黛玉和晴雯都抱憾早逝,而她们的对手——宝钗和袭人——却陪伴在宝玉身边继续活了下去。因为读者向来同情失败者,传统的评论难免把黛玉、晴雯的高贵跟宝钗、袭人所谓的圆滑城府相对照,尤其对黛玉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与赞美。甚至那些主要将小说视为反抗封建罪恶的革命之作的现代大陆批评家,也还令人惊讶地延续了传统上对于宝钗和袭人的非难或敌视态度。在他们眼中,宝钗和袭人是封建主义的走狗,虽然她们真正的罪行仍旧是夺走了黛玉的生命和她应有的幸福婚姻。
83版《红楼梦》中的林黛玉
这种有所偏袒的评论反映了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做法:他们首先把《红楼梦》视为一个爱情故事,并且是一个本应以大团圆结尾的爱情故事。假若带着这种感性思维阅读这部小说,天造地设的黛玉和宝玉的爱情竟然是一场空,我们不免感到惋惜。但如果我们细心读这部小说,就不难发现早在失宠于长辈的危机出现之前,黛玉就已是一副郁郁寡欢、怨气冲天的模样了。即便在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里,她跟宝玉的每次见面也总是以误解或争吵收场,而且这些频繁的争吵并不像贝特丽丝(Beatrice)和培尼狄克(Benedick)、抑或米勒曼特(Millamant)和米拉贝尔(Mirabell)之间的吵闹那样充溢着浓郁的喜剧情调。
贝特丽丝(Beatrice)和培尼狄克(Benedick)是莎士比亚的剧作《无事生非》中的一对情侣,他们最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对于黛玉而言,她与宝玉的争吵充满苦涩,伤透了她的心。这是因为黛玉跟宝玉虽然趣味相投,但气质却截然相反:宝玉积极而富有同情心,具有自我超越的能力;黛玉则以自我为中心,多愁善感,最终招致自我毁灭。对于宝玉而言,黛玉的魅力不仅在于她的纤弱之美和诗人气质,还在于她的偏执之处——多疑善嫉和顾影自怜。这些都跟宝玉开朗的性格完全相反,因之宝玉对她的爱始终带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悲哀色彩。纵使他们能够结婚,两人也不可能得到字面上那种浪漫快乐的幸福:如果宝玉仍旧爱她,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自怜悯,一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中梅诗金公爵(PrinceMyshkin)对纳斯塔霞(Nastasya)的那种怜悯和同情。
《白痴》系19世纪俄国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作品之一。小说对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上层社会作了广泛的描绘,涉及复杂的心理和道德问题。善良、宽容的梅诗金公爵无力对周围的人施加影响,也不能为他们造福,这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的徒劳努力,表明作者企图以信仰和爱来拯救世界的幻想的破灭。
毫无疑义地,林黛玉代表了作者本人非常欣赏的一种美人类型。除黛玉之外,书中至少还有四个女子具有可与之比拟的相貌和感性——秦可卿、香菱、晴雯和那目下无尘的尼姑妙玉。这四个女子或是孤儿,或是幼年即同父母分离。她们中有两三个同岁,并且其实就是在同一天出生的。当然,她们各有显著的个性和特殊的命运。黛玉可以同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位相比以加深读者对她们的了解,但就其多愁善感、自怨自艾的性格而言,香菱与她形成了最为鲜明的对照。
在第一回里,作者把过多的寓言意义加诸香菱(那时叫英莲)身上,尽管她不久便降至次要角色。香菱尚在孩提之时就被一个无赖拐走,此后的生活苦不堪言:先是做薛蟠的丫头,后来成为薛蟠之妾。她备受薛蟠之妻夏金桂的虐待,最后因难产而死。同她相比,林黛玉的境遇要好得多。她初入荣国府时,父亲尚在世,而且她虽然失去了母亲,但周遭的亲戚都疼爱她。但在许多长辈的爱护下的黛玉还时刻有不安全感,而香菱虽然受尽折磨,却在每次被允许去拜访黛玉和她的表姐妹时,显得愉快而又无忧无虑。香菱字认不得几个,但她在黛玉的指点下学诗并表现出惊人的进步,因为她能心无旁骛地忘我钻研。当她品读唐诗名句或构想自己的诗作时,常常近乎心醉神迷的状态。在众姐妹中,林黛玉是公认的有诗才之人,但她写的诗无不带有自伤情怀。在她那首最著名的《葬花吟》中,她将自己视为飘零的落花。一个感伤的自怜的人即使在观赏自然美景时也不会忘掉自己,因之她悲吟道:“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83版《红楼梦》中的幼时香菱
宝钗一来到贾府,黛玉就立即感到了不安,因为宝钗戴着的金锁上面刻的字,同宝玉携带的那块玉上的镌文恰成一对。而且,那金锁的来历几乎与那块玉同样神秘:一个癞头和尚在宝钗还是婴儿时送给她的。由于金锁和美玉预示着一桩美满的姻缘。虽然黛玉明知宝玉在众姐妹中独爱自己,但还是觉得少了一件足以象征他们未来婚事的实在证物。
因此,她一方面开始以咄咄逼人之势对待情敌,抓住一切机会讽刺宝钗拥有金锁之福气;另一方面对宝玉也苛求起来,借用种种托辞刺激他说出爱的誓言,从而打破金玉良缘的象征意义。在黛玉这种经常渴求保证的压力下,孩子气十足的宝玉十来岁便迈入了成年。但黛玉所追求的那种安全感不是仅凭言辞就能保证的,而她又是最规矩的女孩,权且不说无法接受以肌肤相亲的方式予以保证,就连宝玉最无伤大雅的情感流露也会招来她的责备。所以到头来她能称之为信物的,只有宝玉以前送给她的两块旧手帕,而她早在上面题了三首诗。临终前她焚化了这两块手帕——事实证明,这样的信物是完全无效的。
宝玉与黛玉
但不管内心如何焦虑和绝望,黛玉一直保持着一种对自己的命运故作冷漠的高傲态度。在古代中国,出身名门的女孩自然不该对自己的终身大事表现出任何兴趣,但大部分女孩都会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贴身丫鬟,而像《西厢记》和《牡丹亭》中的女主角则更是采取有违礼教的大胆手段去争取她们的心上人。可是对林黛玉而言,连“婚姻”这个词都成了一种禁忌,她不愿谈论自己的未来,即使是在自己的侍女兼挚友紫鹃的面前(紫鹃经常恳求她注意自己的身体并以积极的态度努力实现自己平生的愿望)。
林黛玉的挚友兼仕女紫鹃
黛玉深知缺少一个主动关心自己福祉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但她宁愿独自受苦也不愿去奉承长辈。如果说她确实是一个悲剧人物的话,那么她的悲剧性即在于她那种固执的不切实际与反常的自我矛盾:既想同自己的意中人结婚,又担心自己为此而作的任何努力会招致世俗的非议。对她而言,承认自己在欲望和感情方面敏感而脆弱,对自己而言就等于受到了最大的羞辱。因之她只好以带有攻击性的消极方式来发泄她的情感,渐渐地她的脾气变得更坏,言语更为尖刻,行为举止也更易触犯别人。后来她疾病缠身,兼之朋友稀少,她重新陷入自怜之中,认为自己确实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可怜虫。
中国读者一向把黛玉视作一个迷人的下凡仙女,一个优雅纤丽、才华出众的美人和诗人。他们都以为,对于这样一个世界而言,黛玉显得太过脆弱,甚至对于时常表现得轻率粗心的宝玉而言,她也显得太过完美。他们想把黛玉纯粹看作绛珠仙草的化身,丝毫不为丑恶感情所污染。然而,以这样的形象解读黛玉就把其复杂性格简单化了。虽然曹雪芹也有意把她写成一个超凡脱俗的美人,但当他的笔触随着黛玉身体的日益衰弱而去描绘她那愈发明显的精神病态时,他并没有回避任何生理上的细节。到了黛玉做这场噩梦的时候,她身上所有的青春气息都已消逝殆尽。据她自己所说,她在一年之中只有十个晚上能睡得安稳;而且身体极度倦怠,常要在床上一直躺到中午。她常常流泪,所以她的眼睑经常是红肿的。这场梦成为她通向死亡之路的又一个界碑:那天夜里她咳嗽不已,吐痰时连带着吐出了血。天快亮的时候,她叫紫鹃给自己换一个痰盒儿:
开了屋门去倒那盒子时,只见满盒子痰,痰中有些血星,吓了紫鹃一跳,不觉失声道:“嗳呀!这还了得!”黛玉里面接着问:“是什么?”紫鹃自知失言,连忙改说道:“手里一滑,几乎撂了痰盒子。”黛玉道:“不是盒子里的痰有了什么?”紫鹃道:“没什么。”说着这句话时,心中一酸,那眼泪直流下来,声儿早已岔了。黛玉因为喉间有些甜腥,早自疑惑;方才听见紫鹃在外边诧异,这会子又听见紫鹃说话,声音带着悲惨的光景,心中觉了八九分,便叫紫鹃:“进来罢,外头看冷着。”紫鹃答应了一声,这一声更比头里凄惨,竟是鼻中酸楚之音。黛玉听了,冷了半截,看紫鹃推门进来时,尚拿绢子拭眼。黛玉道:“大清早起,好好的为什么哭?”紫鹃勉强笑道:“谁哭来?这早起起来,眼睛里有些不舒服。姑娘今夜大概比往常醒的时候更多罢?我听见咳嗽了半夜。”黛玉道:“可不是?越要睡,越睡不着。”紫鹃道:“姑娘身上不大好,依我说,还得自己开解着些。身子是根本。俗语说的:‘留得青山在,依旧有柴烧。’况这里自老太太、太太起,那个不疼姑娘?”只这一句话,又勾起黛玉的梦来,觉得心里一撞,眼中一黑,神色俱变。紫鹃连忙端着痰盒,雪雁捶着脊梁。半日,才吐出一口痰来,痰中一缕紫血,簌簌乱跳。紫鹃、雪雁脸都吓黄了。两个旁边守着,黛玉便昏昏躺下。
在这本小说的寓言框架里,黛玉应该以泪还债,但这些眼泪实际上只有自怜之意,并无感激之情。在一个完整的悲剧人物身上,我们应该看到某种高贵的品性,那是一种仁慈或慷慨的品质,一种对自我身份的追寻,让他终究能够认清自我。然而黛玉缺乏的正是这种高贵的品性。从智力上看,她完全有能力获得这种自知能力,但她过分囿于自己的不安全感,因而未能从客观或反讽的角度来观察自己。于是,在小说里她尽管诗意地生活着,但其扮演的角色是为了表现无可变更的感伤可怜,为了充分展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在身体和感情两方面的毁灭。在上述场景中,正如第九十八回里那个更加惊心动魄的死亡场景一样,作者虽然对黛玉的处境极为同情,但与此同时,他在详细叙述她的生理状况的细节时也绝不手软。“痰中一缕紫血,簌簌乱跳”是令人读罢最为难忘的一句。
病中黛玉
在那天早晨的晚些时候,惜春——一位宗教信仰极强,后来出家为尼的女孩——论及黛玉每况愈下的情形时说:“林姐姐那样一个聪明人,我看她总有些瞧不破,一点半点儿都要认起真来,天下事那里有多少真的呢?”当然,整部小说中,作者都在把玩“假”与“真”的对照游戏:与贾宝玉相对应的是一个名为甄宝玉的青年,正如其姓名所透露出的似是而非的意味,他比贾宝玉更热衷于本质实属虚幻的功名,因而显得不如贾家的宝玉真实。黛玉主要是小说写实部分的主角,但因其对真实几乎全然不闻不问,这就决定了她在宗教寓言部分里的重要性。
83版《红楼梦》中的惜春
“
怜悯共情与自我救赎这二者之间的不可调和
”
除少数有鉴赏力的读者外,传统和现代的评论家历来一致认为宝钗不如黛玉值得肯定。近来大陆的批评界,除了一个重要的例外,全都恶意贬低宝钗,认为她与“叛逆的勇士”黛玉相反,是一个被封建主义道德培养起来的狡诈虚伪的阴谋家。这种奇怪的主观态度,正如前文所说,部分是源于一种本能的对感性而非理性的偏爱。
83版《红楼梦》中薛宝钗
宝钗是一个善良而温顺的女孩,但尤其因为她在名义上得到了自己最喜欢的男人,如果有读者罔顾她的优点甚至颠倒黑白,也能理解的。但当我们仔细检视所有被引用来证实她的狡诈与伪善的文字时,便会发现其中的每一段都被故意曲解。宝钗固然不是一个叛逆者,她接受了儒家社会中作为一个女性的角色定位,也相信文人的职责在于通过仕途经济之路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在这层意义上,跟宝玉一样蔑视八股文和官僚体系的黛玉,的确少了些“庸俗”而更受人喜爱。但黛玉对庸俗的轻视不过加强了自己孤芳自赏的倾向,而宝钗对礼教的尊崇,则意味着对自己诗人感性的有意压制。
严格来说,黛玉和宝钗两人在才气上不分伯仲,又都是幼年丧父,长住在贾府多少都有些寄人篱下的意味。如果说宝钗尚能从母亲那里寻得爱与安慰,那么我们也必须记得,她生活在一个并不和谐的家庭中,拥有家庭控制权的是她那无能而又毫无责任感的哥哥。由于她相对早熟,又有不足为外人道的种种麻烦的家事,她必须具备圣人般的忍耐和谦逊,以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公认的道德典范。她是一位诗人兼饱学才女,却终日忙于缝缝补补;她是一位和事佬和以诚待人的朋友,却要忍受家中的敌视和外人的嫉妒;她最终当然是一个完美的妻子,不得不做出牺牲,顺从贾母的意志去侍奉半死不活的痴呆丈夫。
83版《红楼梦》中薛宝钗
尽管过于强调宝钗与黛玉的敌对关系一直是批评界的风尚,但我们也应该记得她们二人公开的竞争在第四十五回就宣告结束了。那时宝钗挂念黛玉的病情,在她面前流露出了真挚的友情。而此前一直把宝钗当作情敌并对其采取攻势的黛玉,这时也很感激地接受了这份友情,同时坦率地承认自己一度错误地对宝钗的善意心存戒备。此后,她们成为最好的朋友。
黛玉与宝钗
她们都处于长辈的控制下,都是对自己未来的婚姻毫无决定权的小人物。即使长辈们更希望让宝钗成为宝玉的新娘,他们也丝毫没有考虑到她的幸福。虽然宝玉曾是一个如意郎君,但当大家正式商议婚事之时,他已经是一个暂时没有希望康复的重病之人。既然贾府太太们仅仅把这场仓促安排的婚礼看作为宝玉“冲喜”的药方,那么,宝钗甚至比黛玉更称得上是这场残酷骗局的牺牲品。薛姨妈不好拒绝这门亲事,只能由衷地为女儿感到难过。宝钗一贯对母亲唯命是从,她“始则低头不语,后来便自垂泪”。对黛玉来说,她有充分的理由怨恨贾母、王夫人和凤姐的恶毒安排,但归根到底也只能责备自己没有照顾好身体以及当初主动疏远了她们;可是对于宝钗所受的委屈和折磨而言,这些长辈们极端的残忍与自私自利则要负全责。
嫁给宝玉之后,宝钗当然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改善她那无法忍受的处境:使丈夫恢复健康,回归常人的情感世界。可是再次从太虚幻境中醒来的宝玉变得如此冷漠,在这种情况下,她自己也就情愿放弃舒适、财富、地位,以及夫妻之爱。她想从宝玉那里得到的(也是袭人想要的),是关怀与仁慈。而最终令她深受打击的是,宝玉这样一个曾经对痛苦特别敏感并以此为自身最可爱的品质的人,现在竟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模样。在重新获得其精神本质之后,宝玉已经变成了一块石头。
宝玉、宝钗的新婚之夜
至此,小说为我们呈现了一场极为关键的哲学争论。这场争论清楚地道出怜悯共情与自我救赎这两个主张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在第一百一十八回的前半部分,当惜春和紫鹃决定削发为尼的消息传来,宝玉冷静地流露出赞赏之意。对于他的反常态度,宝钗和袭人深感痛苦不安,她们原以为他一定会为这两位女子的出家之举哭闹一场:
却说宝玉送了王夫人去后,正拿着《秋水》一篇在那里细玩。宝钗从里间走出,看见他的得意忘言,便走过来一看;见是这个,心里着实烦闷,细想:“他只顾把这些‘出世离群’的话当作一件正经事,终久不妥!”看他这种光景,料劝不过来,便坐在宝玉旁边,怔怔地瞅着。宝玉见他这般,便道:“你这又是为什么?”宝钗道:“我想你我既为夫妇,你便是我终身的倚靠,却不在情欲之私。论起荣华富贵,原不过是过眼烟云;但自古圣贤,以人品根柢为重……”宝玉也没听完,把那本书搁在旁边,微微地笑道:“据你说‘人品根柢’,又是什么‘古圣贤’,你可知道古圣贤说过‘不失其赤子之心’?那赤子有什么好处?不过是无知无识,无贪无忌。我们生来已陷溺在贪、嗔、痴、爱中,犹如污泥一般,怎么能跳出这般尘网?如今才晓得‘聚散浮生’四字,古人说了,不曾提醒一个。既要讲到人品根柢,谁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宝钗道:“你既说‘赤子之心’,古圣贤原以忠孝为赤子之心,并不是遁世离群、无关无系为赤子之心。尧、舜、禹、汤、周、孔,时刻以救民济世为心;所谓赤子之心,原不过是‘不忍’二字。若你方才所说的忍于抛弃天伦,还成什么道理?”宝玉点头笑道:“尧舜不强巢许,武周不强夷齐……”宝钗不等他说完,便道:“你这个话,益发不是了。古来若都是巢、许、夷、齐,为什么如今人又把尧、舜、周、孔称为圣贤呢?况且你自比夷齐,更不成话。夷齐原是生在殷商末世,有许多难处之事,所以才有托而逃。当此圣世,咱们世受国恩,祖父锦衣玉食;况你自有生以来,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爷、太太视如珍宝。你方才所说,自己想一想,是与不是?”宝玉听了,也不答言,只有仰头微笑。
上面这场辩论,在中国的思想界是一场永无休止的争论。孟子和老子都把赤子看作人类的卓越模范。但在老子的理论里,赤子是无知无欲的,而以孟子的观念视之,赤子的可贵之处在于其本身就具有尧舜的所有美德。孟子认为,爱与同情是人生的基本事实,宝钗,以及醒悟之前的宝玉也这样认为。如果不忍(“不忍”一词见于《孟子》)目睹痛苦场面的品质无法检验人性,那什么可以呢?如果一个人可以拒绝心中最本能的驱动,他如何还能保持人性呢?
宝钗回答不了这样一些问题,宝玉也不能在一般的人类理性层面答复她,因为只有把人生置于贪婪与受苦的宇宙哲学体系中,一个人才能看到解脱自己的必要。执着于爱和同情就是坚持自欺欺人——在原初的古代道家思想里,人类没有爱和同情之需要。但宝玉不能把这些告诉宝钗,因为即使对于已经超脱的宝玉而言,要他道出这样的真相也是过于残酷的。
end
活字新书
在任何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中,中国古典小说都是一个突出的方面。它们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要表现;其中有些作品同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一样值得重视。《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共分八章,全面系统地对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了评述,重在阐释,为作品本身的基本理解和欣赏服务。夏志清的评论,侧重阐明小说所反映的“义理”与文化传统,检视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性格;同时他按照自己一以贯之的对文学艺术的严格标准,将其放在世界文学的视阈中,对六部小说进行了小说艺术、结构、文字等方面的深入批评。夏志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鉴赏,在形式与内容、方法与观念上,达到了一个可贵的平衡。本书所开创的研究视野与问题意识,为后来西方汉学界的古典小说研究,奠定了根基,本书实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
名家荐语
“
本书出版之前,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讨论远未实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而夏在这本极优秀的作品中,用扎实的学识和独到的见解,树立了有关领域学术讨论的高标准,令同行以及后来的学者受惠良多。
”
——白芝(Cyril Birch)教授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
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小说的好的评论作品并不多见,而夏教授的这本书极大地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这本书既可当作研读中国小说的入门书,同时也是有关这几部中国小说的第一流的评论文章的系列结集。
”
——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 哈佛大学
成就有生命力的思想